《都灵之马》剧情介绍
都灵之马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1889年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克·尼采在维亚·卡罗·艾尔波特酒店的六号门前驻足。他的目光被酒店外的一个马车吸引。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马车。马车的车夫遭遇到了一匹倔强的马。不管车夫怎么喊叫,马匹根本没有要移动的意思。最终,车夫失去了耐心,拿起了鞭子,朝马匹打去。尼采见到此番情景,挤进人群,冲到马匹跟前,阻止住马夫,抱住马的脖子,痛哭起来。酒店的主人赶来,拉走了尼采。回到酒店的尼采在沙发上安安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了两天。随后,他小声地说了几句话。接下来,就是尼采精神错乱、神经颠颠的十年,由他的妹妹和母亲照顾的日子。谁也不知道,在都灵,在那匹马的身上,在尼采的心理,发生了什么。”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米斯特和皮特必败辛纳特拉:孤注一掷当恶魔呼喊你的名字时你是我的人间至味王中王小心!我要放大招了轻音少女特典我的叔叔IT狂人第二季老海的新生活中产阶级82号古宅星期恋人:前篇吓吓朱莉人设骗局第一季新扎师姐沸腾吧沉沙池狩龙人拉格纳蚯蚓讨厌你的方法我是监护人魔幻车神W底层世界决战犹马镇滇西1944王者联盟之超能力者顽皮鬼2窃听黑幕明月守护者自己的葬礼
“1889年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克·尼采在维亚·卡罗·艾尔波特酒店的六号门前驻足。他的目光被酒店外的一个马车吸引。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马车。马车的车夫遭遇到了一匹倔强的马。不管车夫怎么喊叫,马匹根本没有要移动的意思。最终,车夫失去了耐心,拿起了鞭子,朝马匹打去。尼采见到此番情景,挤进人群,冲到马匹跟前,阻止住马夫,抱住马的脖子,痛哭起来。酒店的主人赶来,拉走了尼采。回到酒店的尼采在沙发上安安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了两天。随后,他小声地说了几句话。接下来,就是尼采精神错乱、神经颠颠的十年,由他的妹妹和母亲照顾的日子。谁也不知道,在都灵,在那匹马的身上,在尼采的心理,发生了什么。”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米斯特和皮特必败辛纳特拉:孤注一掷当恶魔呼喊你的名字时你是我的人间至味王中王小心!我要放大招了轻音少女特典我的叔叔IT狂人第二季老海的新生活中产阶级82号古宅星期恋人:前篇吓吓朱莉人设骗局第一季新扎师姐沸腾吧沉沙池狩龙人拉格纳蚯蚓讨厌你的方法我是监护人魔幻车神W底层世界决战犹马镇滇西1944王者联盟之超能力者顽皮鬼2窃听黑幕明月守护者自己的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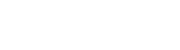
能看完就是胜利
五星;匈牙利艺术片大师贝拉塔尔的收官之作。一部需要耐心看完的神作,电影实验性强烈堪比任何哲学名著,每一个黑白的镜头都是导演想要表达的反创世纪逆向工程,在第六天光也消失的时候,一切冗长重复艰涩也结束。
电影是大众艺术,弄成这样,还不如写篇哲学论文。很多故弄玄虚的人不敢说实话,那就祝福你天天看这种电影
我说我看懂了这电影那就对不起我的智商,我说我喜欢这电影就对不起我两个小时内没停过的动森。这电影没给我什么深刻的内容,但当我看着女人每天出门打水的时候,我在动森里正给我那一大片蕃茄田浇水。我那一瞬间想着,动森里面的“我”每天都在浇水钓鱼潜水,他有没有在那一瞬间想不跟着我的手柄方向和我的意念走;我每天打开动森就为了干这些事,我有没有在一瞬间想过换种玩法;我每天醒来到躺下其实什么都没做,我有没有在一瞬间想过换种活法。当我陷入这样的想法后我就会开始内耗,而当我永远把第二天的生活和自己的未来当作灿烂与美好的,我又会觉得自己有了活力。取景地哪里找的,呼啸山庄剧组呈现的风都没这个厉害,下次重温呼啸山庄小说我就拿这电影当背景音
要不是被按在电影院肯定看不完,像当年看塔克夫斯基的感觉,预习了死亡的结局,应该更从容不迫。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镜头
我真不知道怎么给星,所以这个三星纯粹就是不知道的结果。我完全看不懂~~~完全完全看不懂~~~~~花了三个星期看这2个半小时~~~~~看不懂~~~~~~
没有忧郁而死,在通往忧郁的过程中,已死。贝拉塔尔的片,无论打几星,都没人说你。
幻想了几次配乐加现代舞,这大概是拯救大师烂片的一个路子
8.11 中国电影资料馆。9/10 粗粝质感的黑白影像 厚重低沉阴郁绝望的配乐 全方位多视角的长镜序列 循环往复单调乏味的日常 风沙呼啸肆虐永不停歇 世界自光明诞生 又隐入无尽黑暗 于一片混沌之中 重构经典创世神话 是导演对尼采“上帝已死”哲学命题作者性的表达 想起大学时期某次自习时 教室内闯入一位学长 他在讲台上宣讲 为读书协会纳新 并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极力推崇 表示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 那我们整个大学生涯将是虚度时光 毫无意义 后来 这位年轻同学被导员请出了教室 联想到电影中父亲和买酒男人的对话 真是奇妙的互文…
恶心的要吐。如果这也叫哲学电影,怪不得如此多庸众藐视哲学,如果还原日常生活琐碎和无望,就是对尼采超人哲学的回击,那么如此的哲学太低级,也太猥琐了。还有,尼采,你为何说你蠢呢?你已经捍卫人类尊严了。你的反抗,绝不是这部猥琐片的导演能驳倒的。向您致敬!
目前还是维持原观点不变:根本就是一场无任何意义的影像灾难。
每个人对尼采的理解都不一样吧
风在猛烈的吹,盘中的土豆被捏碎吃下,马开始绝食,井枯竭了,风仍在险恶地刮着,光消逝了,一切都没了,世界终结了,尼采疯了。 9.3 ★★★★☆
看睡着了 清醒过来马上倒回去 结果发现什么都没错过 还是那两个画面
随手数了一下,大概29个镜头,充分利用了极为封闭、有限的空间,每一个镜头,即使是重复的情景,也被分别赋予了不同的并且递进的主题,闷到实在喘不过气就不禁会想:面对机械枯燥毫无意义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活着?看到父女两徒劳地试图点燃油灯,有点明白了贝拉塔尔的答案:我们并不是要活着,我们只是在活着,而已。
看画质,我以为是六十年代的电影,看了简介,发现更不知道演的是什么了
为了迁就长镜头,牺牲了景深、锐度、光线、表演。而且这不是一种交流的心态,完全是高高在上地撒癔症,因为太闷了。
睡了一小觉,睁眼发现换了个机位又换了一遍衣服,过一会响起跟前面一模一样的音乐,就退场了[拜拜]。而且,煮那么大的土豆还尼玛不吃完扔掉!!!一箱子土豆你特么就不能挑个小点的煮吗!!!吃多少盛多少!!!盛多少吃多少!!!
反正我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