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摄像机》剧情介绍
隐藏摄像机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乔治(丹尼尔·奥特尤尔 Daniel Auteuil 饰)与妻子安娜(朱丽叶·比诺什 Juliette Binoche 饰)、儿子皮埃尔一家三口的平静生活被乔治从家门口捡来的录像带打破,这盒录像带显示有人静静地注视着乔治家的一举一动。很快,更多的录像带 和恐吓性质的明信片寄到了乔治及家人手上。乔治对看不见的敌人殊为紧张,开始小心保护儿子,并且为录像带的内容指引,回想起多年以前,差点成为母亲养子的阿尔及利亚遗孤马吉德。乔治怀疑录像带的始作俑者即为马吉德,于是登门拜访,却引发了意外的结局…… 本片获2005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费比西奖等二十余项专业褒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堕落天使2:和平卫士爱情语言学浴血无名·奔袭双世萌妻龙凤斗妙警贼探第三季影后风云七岁那年的初次见面兼并天空市凶案第三季成吉思汗我是农民女人百态盲流感恶棍少爷别碰我野人无法满足、停不下来遗忘者之绝命狙击1915年的卡蜜儿苍狼之特战突击真正的痛苦向往的生活阿倍野桥魔法商店街三面形医摩亚男孩第一季少女的异想日记疼痛难免圣地亚哥的白拐杖薯唛大贼金麦侦探社
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乔治(丹尼尔·奥特尤尔 Daniel Auteuil 饰)与妻子安娜(朱丽叶·比诺什 Juliette Binoche 饰)、儿子皮埃尔一家三口的平静生活被乔治从家门口捡来的录像带打破,这盒录像带显示有人静静地注视着乔治家的一举一动。很快,更多的录像带 和恐吓性质的明信片寄到了乔治及家人手上。乔治对看不见的敌人殊为紧张,开始小心保护儿子,并且为录像带的内容指引,回想起多年以前,差点成为母亲养子的阿尔及利亚遗孤马吉德。乔治怀疑录像带的始作俑者即为马吉德,于是登门拜访,却引发了意外的结局…… 本片获2005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费比西奖等二十余项专业褒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堕落天使2:和平卫士爱情语言学浴血无名·奔袭双世萌妻龙凤斗妙警贼探第三季影后风云七岁那年的初次见面兼并天空市凶案第三季成吉思汗我是农民女人百态盲流感恶棍少爷别碰我野人无法满足、停不下来遗忘者之绝命狙击1915年的卡蜜儿苍狼之特战突击真正的痛苦向往的生活阿倍野桥魔法商店街三面形医摩亚男孩第一季少女的异想日记疼痛难免圣地亚哥的白拐杖薯唛大贼金麦侦探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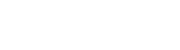
#2025奥地利大使展# 大光明电影院,4.0分。叙事外有两个高度重合的偷窥与梦境的机位,除了一些城乡差异外,似乎指向故事的催化来自记忆与被人注视的恐惧两种压力的不断挤压(这也是视听上给予观看者的一大压力);同时主角的身份又意味着公众属性,一切诉说的言不由衷,是面对压力维持现状的惯性,但当压力丝毫不停切表现为无处不在时它就无法走向平时的微妙平衡。但我或许觉得影片本身涉及的回忆本身,其实需要通过知识分子的建构(比如阿尔及利亚独立)才能呈现为(历史)弥漫的恐惧,整个推进过程好像有点使不上劲儿…… 所以我倾向于虽然出现了哈内克式突如其来的压力爆裂场面,但整个后半段有点流俗了,让人更多落入了“何至于此”的中产道德剧的焦虑。
人性的自私和虚伪是可以超越种族仇视而存在的,本片过于美化在大民族夹缝中生存的少数民族
法国有些电影实在是闷得很,这部隐藏摄像机暂停了3次以上勉强看完。我们都会犯错,也可能会做一些昧良心的事情,这都不可怕,就怕不醒悟,将错就错。承认错误,检讨自己,反省,然后重新出发,这才是需要做的,可是总有些人偏执的认为自己做的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并找各种理由证明自己是对的。
开头10分钟看起来觉得沉闷疲塌,往后复往后,越来越抓人;导演冷峻叙述的底下始终紧绷着黑暗的内核,慢慢释放紧绷的力道可谓是拳拳到肉。
不能说不好,只是和预期的不一样
心不在焉地忍受悬念的煎熬和无配乐长镜头少台词的克制处理,终于等来了57分钟处据说当年在戛纳放映时让许多观众吓得跳起来的惊人一幕。117分钟够长了,哈内克还不把话说明白,遮遮掩掩折磨人。电影公映后不久巴黎发生与之相关的骚乱暴动事件。
失望。实在不知道在说什么。
3.5 以小见大,从家庭裂痕与危机蔓延向历史罪孽的隐喻,冷峻的窥伺录像宛如一个不带感情的影像审判之眼,洞见中产阶级虚伪属性的同时又将个体、社会用噩梦连接,触发因果勾连的被隐藏的集体记忆。从貌不惊人的监视录像带一步步追溯到社会矛盾的历史源头,很有野心的叙事架构。但成片内容确实略漫长乏味,有看困。
让我失望的电影。
没有凶手,称得上悬疑?
情节很有些莫名其妙,剧中人物的反应让人摸不着头脑:1、男女主竟然从没想过去找一下偷拍的摄像机机位?架在他们家门口的机位拍了不止一段寄给他们啊!2、在马吉德家里的摄像头拍下的内容,马吉德父子都矢口否认和自己有关,他们tm是脑子有病啊,这不是睁着大眼说瞎话么?这有什么可悬疑的啊??
He's using the camera itself to crystalize a prevailing horror, timeless and universal. Who cares about the practicality?
(4.2/5.0)割喉加重了本片的陈词滥调感——“平静中爆发”的拍法已经看得够多了.
令人难忘的长镜头,那只被割喉的公鸡和自刎的Majid。历史、社会、家庭遗留的触目伤口始终难以愈合,哈内克式惊悚冷冷的很锋利,哪怕是《爱》也时而瘆人
私人评论电影的条件,除了开放式结局,最大的悬疑没有得到解释,就是耍流氓。
个人并不喜欢这种令人费解的影片,尽管众观者将作品拔高到种族隔离等等高度,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了背景新闻的隐射含义,但仍然不以为这就是部值得重温或值得推荐的作品。故弄玄虚的摄影机,而且不合情理。套个高尚主旨就显得牛鼻了?那岂不我们的政治课都很牛鼻?
9.25 一个奥地利人,敢拍阿人受难这么provocative的题材,哈内克带种。每次看他的电影都是呆呆地盯着屏幕,心里喃喃地说:这个老头子好厉害……可貌似还是比伯格曼差了那么一点。男主坦白过去有点太仓促了。
想起了狙击电话亭和《云破处》。看了一半觉得看懂了,看着看着又看不懂了,看完了也不知道是看懂了还是没看懂
7.9/10 (时隔半年的补标)后半段把隐私侵犯升格为道德侵犯的中产危机似乎失去魅力
看不懂